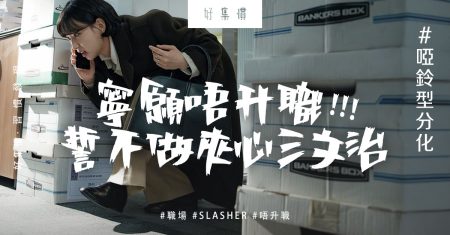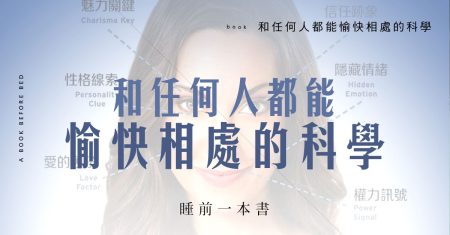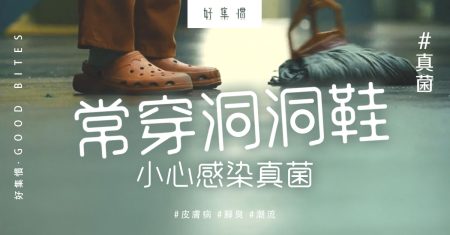很多人以為「旅居」只是拉長版的旅行,但只有當你放慢腳步,放下旅遊景點帶來的多巴胺,用生活者的角度去感受一座城市,才會真正明白旅居的意義。
剛剛在台北,我體驗了當地著名的「追垃圾車」生活。他們的家居垃圾分為三類:一般垃圾、資源回收與廚餘,三輛垃圾車會同時到來。我一聽到熟悉的「給愛麗絲」音樂,就趕快拿着分類好的垃圾衝下樓。到達收集點時,街坊們已整齊排好隊伍,畫面井然有序,直到我倒廚餘的時候⋯⋯廚餘需倒入深而大的桶裡,並將膠袋拆開。我事先聽從本地人建議,將廚餘用雙層膠袋包好冷藏在冰格中以防發臭,果然是一個聰明的方法。但當我手忙腳亂地打開那個像冰磚一樣的廚餘袋時,一不小心滑手,那塊半結冰的廚餘硬塊從半米高處跌進大桶,濺起一片濕黏的液體,正中我臉上。台灣的廚餘一般用作餵豬,而現在的我竟然慘成了那頭豬⋯⋯我閉氣、強忍呼吸,努力不去聞那混合各家廚餘的芬芳氣味。但現在回想,那正正是旅居澀中帶甜的滋味。



「十年後,我們又會身在何方?」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命題。兩年的旅居生活讓我體會到,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城市,只有適合自己的生活。台灣人熱情親切,生活便利,但夜晚機車聲震耳欲聾;日本乾淨整潔,人卻略顯冷淡;馬來西亞文化多元,生活悠哉,但汗流不止成了日常。正是這些不完美,讓我學會欣賞每一種生活的美好:多一點包容,少一點比較,每到一個地方都是一個新開始。
我記得在福岡的第一晚,跟朋友到一間燒肉店吃飯,坐在吧枱兩旁,都是說廣東話的香港人。雖然身在異鄉,大家卻默契地「裝作不認識」,這是一種香港人常有的尷尬避忌。但那晚因為一塊高麗菜,我們打破了沉默。我台灣朋友日文流利,她輕聲對我說:「老闆一直在偷笑,原來他們在笑左邊那桌的客人竟然把高麗菜放上爐烤。」原來在日本,高麗菜通常是沾醬生吃的。我一邊看着差點燒着的菜葉,一邊禮貌地提醒對方,也順勢跟老闆說我們也是香港人,不太懂這邊的吃法。沒想到就此打開話匣,加上酒精的化學作用,老闆谷口先生打烊時忽然問:「今晚很開心,要不要一起去樓上的酒吧?」我猶豫了三秒,心想:我不就是為了這些難忘經歷才選擇旅居嗎?「For sure,行きましょう。」我笑着回答。

那間酒吧極為地道,不熟門路絕對不敢走進去。桌上已擺好各款烈酒和烏龍茶,還有一位專人為我們倒酒。谷口先生興致高昂,遞來點歌機:「Let’s sing!」當下我傻眼了,竟然要唱歌?我心想:如果點陳奕迅,變成獨角戲怎麼辦?當然不可以!(看來我在日本待久了,漸漸學會了「閱讀氣氛」。)這時谷口先生唱起了一首熟悉旋律:「如每過一天,每一天這醉者…」原來這是《每天愛你多一些》的日文原曲。對啊,香港的經典粵語歌,很多原曲其實來自日本!

我接連點了幾首舊歌,「風繼續吹,不忍遠離⋯⋯」、「冷冷雨 wooo,沒焦點⋯⋯」竟然越唱他們越有共鳴。谷口先生和酒吧裡的日本中年顧客紛紛驚訝:「為什麼你們會唱這些?」看來我小時候最痛恨我爸聽的舊歌,在這刻成了一道橋樑,把香港和日本,過去和現在連在一起。我們一邊用日文一邊混着廣東話合唱,一晚過得像一齣日劇。
這晚的經歷很神奇,成長在不同年代、不同地點、不同語言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我們,竟然會找到共鳴,對了,就是「共鳴」!
那刻我明白了,異鄉的旅居生活,最可貴的就是找到共鳴。
我們總是外人,難免會有孤獨感。孤獨,其實是因為我們與身邊的人和事之間沒有產生連結。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說得一口流利英文,在英美總不如在台灣般親切?答案也許就是共鳴,也許就是周杰倫、五月天、F4、《流星花園》、瓊瑤和九把刀的小說……這些共同記憶。
異鄉的生活要過得開心,就是要設法與所在地產生共鳴。旅居,是學習與異地共鳴的過程。十年後,我們會身在何方?誰也說不準。但在旅居的日子裡,我們至少有機會走慢一點,試探、學習、感受,然後更有勇氣去迎接下一站的生活——不論身在何處,哪裏讓我們安心,那裏就是吾家。

撰文、照片:孝仔 @mariohau